长沙男童遇害案:围观者与恶的距离

没有等来的朋友
▲▲▲
从二年级开始,罗琪就可以自己上学了。在罗家人看来,这实在算不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从罗琪家下楼走到上学的雅塘村小学,不过900米的路程,这其中,超过300米都在小区里面,剩下的路绕着一个小山包蜿蜒,大马路的路口只有一个。
从一年级搬到汇城上筑之后,这条路罗琪已走过四年,沿途穿过一家粉店,两个早点摊,还有三家商店。三家商店主要做的都是学生们的生意,老板们也都认得罗琪,“我晓得,孩子王嘛”。
在班上,罗琪是家长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考试从来是班上的前两名,作业做得又快又好,他还在校外报了奥数、编程、美术和书法这些课外班。他还又高又帅,是运动健将,运动会上跑得最快的一个人,而且人缘极好,大家都听他的。”这是住在同一小区里同班同学童童的爸爸童辉一口气对他做出的评价。

罗琪家里,奖状贴了一面墙
童辉原本没留意过这个孩子。汇城上筑位于长沙的城市边缘,小区里的建筑关系有点复杂,西南侧是原来国企的老单位房,外墙斑驳,房屋结构也不是很好,但拆迁就是拆不动,所以开发商就在周围盖起了商品房,一个物业公司把这些房子圈在了一起。老房子的物业费是0.5元/平米,商品房是1.5元/平米。童辉在一家媒体公司上班,大约在10年前买下了5号楼100多平米的商品房。
罗琪的父母是从湖南新化来到长沙的打工者。 罗琪的三叔罗平波告诉我,罗琪的妈妈自罗琪出生就没有再找工作,而他父亲这些年陆陆续续打的也只是零工,每个月不过两三千元。原本一家三口挤在更靠近郊区的一处月租仅400元的开间里,直到罗琪要上小学,为了离学校近一些,家里咬着牙,每月800元,租下了这套包含一间书房的位于老房子六楼楼顶的三室一厅。两栋楼在小区里隔了100多米,刚开始的时候,在商品房里住了五年的童辉,并不认识罗琪一家。
和很多年轻的家长一样,童辉把自己关注的重心完全放在了自己女儿身上。在他眼里,自己的女儿不只是班上个头最矮的一个,而且脾气大、爱哭,“虽说这个年龄咱们不能用成熟来要求她,但怎么看她都有点像小公主,没心没肺的”。担心都市相对封闭的环境对女儿的成长不利,童辉还围绕女儿组织了不少家长间的社交活动。按他本来的设想,小朋友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是大人关系的延续,大人们之间聊得来,动不动在一起吃个饭,孩子们自然关系就好了。
但女儿在班上人缘一直也就那样。直到二年级,他从女儿嘴里听到了罗琪这个名字,并且频率越来越高。“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都是一些日常的琐事。”有时候,是童童在学校被别的同学欺负了,罗琪帮她出头,有时候则是罗琪惹到她了。童辉印象中两个人最大的矛盾是有一天童童回家说,罗琪借了她一块钱不还,她发誓再也不理他了,但第二天,童辉看见两人又像没事人一样一起从学校里跑出来。
在童辉的印象里,他们一块玩的有一帮朋友,但到家里来找童童的,永远都是罗琪。童辉说,暑假的时候,家门一天能被罗琪敲响三次,“每顿饭后都有一次,每次进来他第一句话都是:童童妈妈,我能带童童下去玩吗?”一度把童辉都给敲烦了,不得不敲打罗琪两下:“童童作业还没做完,以后你吃过中午饭后再来找她吧。”
童辉记得,三年级的一天,自己的小公主有一天回到家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以后可以自己上下学了。”从此,每天中午1点多,“童童,童童”的喊声就雷打不动地每天在楼下响起来。

罗琪就读的小学
在罗琪口中,童童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今年老师布置作文,让写“最佩服的一个人”,有人写了科学家,有人写了自己的父母,罗琪写的是“我最佩服的是我们班娇小又暴躁的娇娇女——童童”。童童在那篇文章中的形象并不怎么好,虽然跳芭蕾舞时像一只天鹅,但是在游泳池里她像一只“笨鸭子”。他还认真记载了童童在1.4米水深的泳池里喊救命的糗事,但是,这都不妨碍“我仍然很佩服她”。童辉觉得很好玩,特意给这篇作文拍了照。
这就是孩子的友情,也是让童辉作为成年人颇为羡慕和感慨的,“只有孩子,形容友情时能毫不犹豫地用出最字,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朋友就是唯一的,好像只能够取代,不可以共享”。
11月5日原本是平常的一天,老师刚通知了一个好消息——班上选了两名学生参加编程大赛,罗琪是其中之一。这天中午,正好没什么活儿待在家的爸爸见到罗琪罕见地吃光了一整碗米饭。
中午1点20分,童童妈妈听见楼下传来熟悉的喊声,这是她听见罗琪发出的最后的声响,一切都和往常一样。这天下午有美术课,童童妈妈花了点时间给童童找出来了水彩笔,下午要带,童童在1点30分左右下了楼,但是,她没有看到一直等她的朋友,她被一个老太太喊住了,老太太让她赶紧走后面的一条小路去学校。
致命的相遇
▲▲▲
事后证实,一些危险的讯号并没能传递到17层的童童家。
对于住在五号楼对面六号楼二层的黄菊来说,异变是伴随着一声吼叫出现的。她起初以为是夫妻吵架,走到窗户旁看到,三四米之外的马路对面,一个大人坐在孩子身上,搂着脖子,正拿着螺丝刀击打。她不认得罗琪,也不认得打人的男子,但她听到孩子喊了“救命”。
她本身也是一位母亲,立刻朝对方喊道:“不要打小孩,会出人命的!”但听到喊声,男子突然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她,她害怕了,嗷嗷地叫着,“本来我想拿个雨伞或者扫把出去的,但是这一下突然害怕了”。她只好立刻报警,几乎同时,她听到楼下有邻居给物业公司打了电话,通话记录显示,那时是13:30。那个时候,她看到窗外陆陆续续有人往五、六号楼中间这条小路上聚集,“有的人在朝凶手喊话,有的人在朝孩子喊话,说你要听话、认错,但都没有人敢走过去”。
第一个路过的人是清洁阿姨李莉,她本来也在边上等了几分钟,喊周围的人赶快报警,但她赶时间去附近的超市上班,“下午1点50要打卡”。五、六号楼中间这条小路是她的必经之地,正好当时一辆轿车驶过,她跟着小轿车跑了过去,最近的时候,她距离行凶者不到一米,那辆白色的轿车,在中间减了速,但是没有停。李莉看到小孩的脸憋得紫红,舌头已经吐了出来,男子看到她,双手举起螺丝刀摇晃着,李莉再不敢停下来,警方在找她录笔录之后核实了监控,确认那时是下午1点33分。
小区的保安亭设在小区门口,距离事发地大约200米的地方,是一个封闭的岗亭,但那里看不到小区里的监控。53岁的保安潘浩是在下午1点36分接到物业公司负责人秦主任的电话后从大约300米外的车库赶到现场的,跑到一半,他想起来没有带制服歹徒的工具,又折返回去取了一张网,但是当他和秦主任赶到现场时,仍然没有第一时间制服歹徒。
“那时候整个现场的氛围已经变了。”黄菊在家里听见外面吵吵杂杂的声音大都在讨论谁认识这个凶手。建筑工人黄觉本来在给小区做翻修外墙的工作,看见打人的那一幕和工友拿着木棒赶过来,本来企图制伏凶手,但是每次试图靠近,对方就拿螺丝刀朝他自己胸口比划,周围有人劝他们:“万一男子因为你们介入而自杀,说不定还会有麻烦。”他最后放弃了动手的想法,他听到周围有人说,这个男的是精神病犯了,已经有人去喊家属了。
据说最开始认出冯广身份的是小区里和他父亲一起开摩的的陆师傅。他告诉本刊,之前一起跑活儿时,听冯师傅提起过自己的儿子有精神病,之前甚至走丢过几次,那天他正准备出门拉活儿,看到这个情况赶紧给冯师傅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坏了’之后,冯师傅赶快喊我过去”。
在这起悲剧中,双方的亲人几乎都是最晚知道消息的。 直到1点40左右,童童妈听见屋外的声音越来越吵,打开窗户视线又正好被一颗大树挡着,她才决定下楼看看,一看把她吓了一跳,是罗琪,她赶紧朝着周围的人喊:“你们快去救人啊!去制服那个疯子啊!”周围的人告诉她,孩子已经没救了,那个人是精神病。她赶紧给罗琪妈妈打了电话,没敢说实际情况,只说:“你快来,琪琪好像出事了。”
冯广的父亲在大约10分钟后骑着一辆黑色电动车赶来。他把电动车停在前面的车后面,走到冯广跟前,把脸凑过去低头看了一眼,随后抓住了冯广甩螺丝刀的右手。包括秦主任、潘浩等四五个人上前抓住冯广的手、脚,把他按倒在地,冯广挣扎着“哇哇”大叫,不时抖动着身体。
罗琪的父母几乎是最后赶到现场的人。 于是有了那段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的视频,罗琪的母亲坐在一摊血里,抱着罗琪,颤抖着,哭嚎着,不停地发出哀鸣:“我的崽……快点喊医生来!”
13:50,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雨花亭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安排赶来的“120”做急救措施,随后将罗琪送到了医院。15:25,宣告抢救无效死亡。
罗琪的三叔罗平波提供给本刊的尸检报告表明,法医对尸体检查后发现,孩子头部、颈部有明显软组织挫伤,右大腿内侧有一个破裂口。头皮下大面积血肿,颈部及肺部都有大面积出血。通过尸检,法医认为死因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但更多的受访者称,这些描述远不足以描述罗琪的惨状。
有的人提起冯广,说他不是每天还去幼儿园接送自己的侄女吗,怎么就成了神经病了?小卖部老板说:“平时来店里买东西,有说有笑的,完全看不出来。”冯广的父亲也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天吃过午饭,他要给电动车去换电池,老伴搭他的车出去找点零活儿。他们完全没意识到冯广独自在家有什么问题。
但冯广还是独自走出了家门。据澎湃新闻援引警方调取的监控录像,11月5日13时30分,罗琪来到童童所住的五号楼电梯厅。此时,冯广从五号楼三层的家里出来,手持一把长约20厘米的螺丝刀,乘坐电梯下到电梯厅,与罗琪相遇。
电梯厅里的监控并没有保存下来,从电梯间到外面总共不超过20米的距离,没人知道这20米距离发生了什么。 人们只能看到主干道上的监控显示,罗琪跑出单元楼,摇摇晃晃往外面的道路跑。楼梯一共有8个台阶,“啪”的一声,罗琪扑倒在了最后一个台阶上。来不及等他起来,一个巨大的身躯压了下来。
班上跑得最快的罗琪,人生最后的轨迹是一条跌跌撞撞的“蛇形”。他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和黑色的运动鞋,都是今年新买的,这些连同散落一地的水彩笔,是他挣扎求生最后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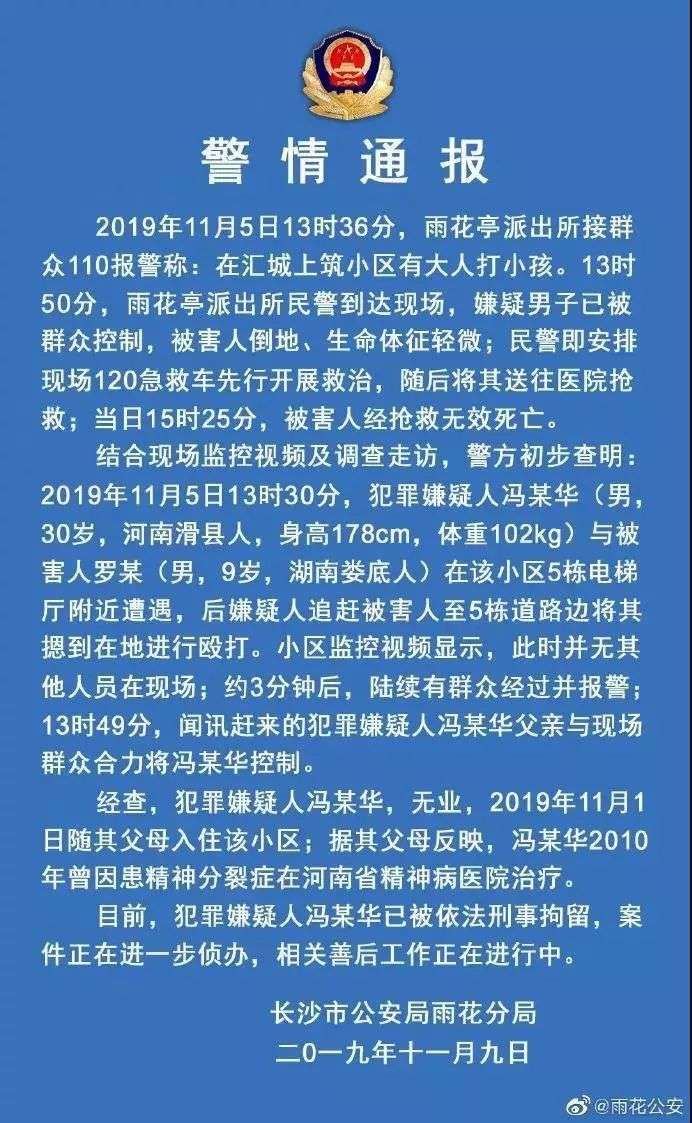
围观者与恶的距离
▲▲▲
事情发生后,小区的气氛有些微妙。
因为视频在网上的传播,巨大的压力涌向小区居民 ,我下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随口一句,“你要来的是这里哦,这个小区人的素质真是高,见死都不救”。马上有小区里路过的居民表示不满:“轮得到你在这说风凉话,你到时候就真敢往上冲吗?那个时候小孩子已经死了。”
“死没死轮得到你宣布吗?再说就算死了就可以允许他继续那样做吗?你们几十个人,连一个赶上去的都没有,保安都不敢上,真给长沙丢人。”司机师傅不甘示弱。

家属一度认为是围观者不作为才最终导致自家孩子的悲剧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第一个路过的李莉反复说,她经过的时候,男孩已经没有动静了,但男人依然在捶打身下的罗琪。她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实在是不敢和近一米八的壮汉搏斗。罗琪的三叔罗平波后来看了监控录像,告诉我,孩子从被凶手骑到身上到不再动弹,只有几十秒时间。这些连带着警方通报中“该路段最初没有围观者”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小区居民的心理压力。然而,也有人心里过不去那个坎。
11月7日傍晚,小傅在汇城上筑的业主群里发出了一条1000多字的消息。这位居民证实,他听到了居民和打人者的对话,他当时也以为这是一对父子。下楼围观时,发现大部分人也和他一样没有搞清状况,“有人说是父亲失手打死了孩子,有人说不要上去,孩子已经死了”。
在这封长信中,他说道:“我内疚、自责,想对孩子的妈妈说声对不起,我当时没有冲上去,这两晚一直在反思,我并不是无情冷血之人,为何当时却没有上前,我没搞清楚状况,真的真的对不起。为自己的没上前的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持这样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小区业主组织的自发捐款中,有人捐出1000元,自觉对这个家庭有所亏欠。

11月11日是“头七”,家属和社区人员在小区纪念罗琪
长沙汇城上筑的居民们都自认绝非生性凉薄。童辉说,我们有时想我们绝不比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小区的道德水平更差,可是事情就发生在你这里,如果当时谁积极一点,结果是不是可能就不一样了?
而在灾难的另一端,同样是一个艰难求生的家庭。冯广的父亲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达了对罗琪一家的亏欠,愿意尽一切可能去补偿。他说自己老家是河南滑县农村的,很大程度上,他对于儿子的精神病,并没有什么办法。在11年前,儿子在高中复读阶段查出精神病时,有耳鸣的症状,在县医院住了一周的医院,医生才说可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冯父说,冯广随后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和住院治疗,最开始也不过就是在延津县下面一个乡的卫生院住了一个月院。直到2010年冯广才在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就诊,一次4个月,一次2个月,正式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他说自己从来不是任由儿子病情发展。本来儿子在这次住院之后坚决称病已经好了,拒绝继续服药,是家里每天把医生开的药掺进饭里,如此过了这些年。因为药物遇热失效,全家跟着儿子吃了好几年冷饭,直到今年觉得儿子情况好转,才停了药。
而这恰恰是精神疾病治疗的大忌。 精神病专家、绍兴市强制医疗所(原绍兴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病区副主任刘晗告诉本刊,减药要经过医生的综合考虑,根据病情的缓解程度、药物的副作用、病人能不能配合医生这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然后再减药停药。另外一名精神病专家则告诉本刊,就像感冒一样,精神分裂症也会有复发的可能。
据澎湃新闻援引办案民警的表述,冯广被抓后,唯一一次情绪稍微平稳时,向办案单位交代自己“追杀”罗琪的动机时说:“手中拿着改锥,比划着,突然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他,这个就是冯家的传世宝剑,他要保护好宝剑,那男孩想要抢走宝剑,他要和他比试,捍卫家传宝剑……”

犯罪嫌疑人
就在冯广行凶的两天前,11月3日,冯广还曾经一度在深夜10点失踪了,冯广的父亲甚至一度报了警,全家人找遍了火车站、橘子洲,甚至因为他爱钓鱼,还去了河沟里找,都没找到。直到第二天有好心人打电话给他,他才把儿子找回来。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业主群里有人责问物业、责问社区,为什么辖区里住着一位随时可能失控的精神病患者,而没有任何备案?社区负责人对媒体表示:“针对本市户籍的精神病患每年会安排四次随访,但是对于流动人口目前实施起来尚有困难。”
当悲剧发生后,并非没有常识和教训可供普及和分享,比如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湖南省法学会程序法学研究会会长黄捷告诉本刊:“像这种正面发生的侵害和危险,其他人也好,受害人也好,受害人的近亲属也好,可以对他采取正当防卫的手段。正当防卫就是对他也造成一定伤害的手段,来停止这种危险和威胁。有一个‘紧急避险’的原则在这里可以适用,就是可以牺牲一个小的合法利益来保护更大的利益。因为当时情况紧急不晓得冯广的情况,那么采取一些措施都是法律允许的。”
但是观点和经验易于分享,每个人心灵上的诘问却难以消除。 当灾难过去一周,律师的观点证明“围观的人们确实没有责任”,评论家们说出“要更多地去鼓励那些见义勇为的人,而不是批评那些围观的人”的时候,发出1000字长信的小傅并没有迈过心中的坎。他拒绝了我的采访,“我现在静不下来,再去说什么,好像都是一种伤害”。
当罪恶发生的时候,没有人是罪恶的一部分,可是人们距离罪恶又有多远呢?是一盒药物,一个登记簿,是10分钟,还是100米?
那天唯一的介入有可能来自童童,在小路上走到一半,她用自己的电话手表给自己牵挂的朋友打去了一个电话。晚上回到家,她和妈妈说,电话里传来“啊,啊”的声音,她吓得赶快挂掉了。她的电话手表,之前每天和罗琪聊个不停,现在她总是不断拿起又慢慢放下,童辉希望女儿永远都不知道那两声意味着什么。
(责编:番茄捣蛋)